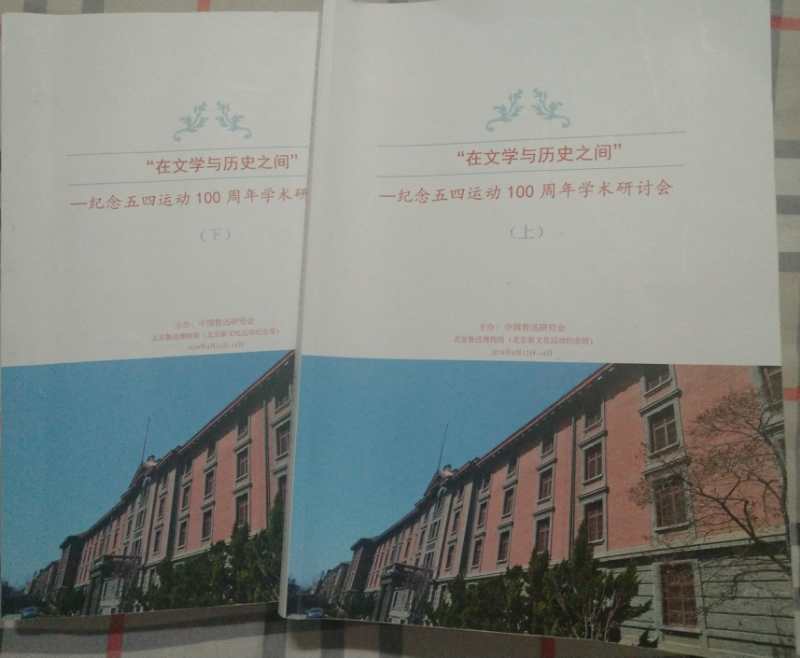2019年5月4日,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。日前,中国鲁迅研究会与北京鲁迅博物馆(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)一起主办了“在文学与历史之间”——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。来自国内各高校、社科院所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,共同探讨100年前的那场开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文化运动。主办方将他们的90余篇学术论文汇集成册,其中研究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文学创作的学术论文就多达20篇,另外五四女作家的“娜拉书写”在当时社会掀起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大讨论,也成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亮点。
不同时空的作家可以凭作品对话 故乡书写是文学创作的恒久主题
北京青年报记者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注意到,分组讨论共分三个小组,除了对“五四”的综合研究及新文化人物研究以外,有一小组专门就鲁迅研究进行学术探讨。这其中,包括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玮提交的论文《再造新文学与后五四时期的鲁迅》探讨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撰写的论文《
张永辉表示,不同时空的作家可以凭作品对话,故乡书写是文学创作的恒久主题。“故乡”可以分为三个层面:第一故乡是人文故乡,故乡人是主要承载者,母亲常常是源头;第二故乡是童年时的自然环境,大自然是主要承载者;第三故乡则是成年人更广阔精神世界的承载处,可以是职业、事业、工作岗位、居住环境,也可以是更为抽象的愿景、志向、精神追求、思想信仰、民族追求、人类关怀等。第一故乡具有人文性,第二故乡具有自然性,第三故乡则具有建构性和精神性。
在他看来,鲁迅的《一件小事》《无题》显示着构建第三故乡的努力;刘亮程的《对一朵花微笑》显示着接纳第二故乡的努力与建设第三故乡的可能;刘慈欣的《带上她的眼睛》则显示着恢复现实与想象中第二故乡之美的努力。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显示出重建与世界的联结,即重整自我、重回故乡的心路历程。“上述几篇作品中对世界的接纳、故乡化、内我的调整、外我的更新与扩大,都折射着三位中年作者试图调整自我、调整内我与外我关系、接纳或建构不同层面故乡世界的努力。”
主办方将征集到的90余篇五四运动学术论文汇集成册
北京鲁迅博物馆(北京新文化运动馆)副研究员何巧云则在论文《鲁迅故乡情感之历时考察》中写道,爱或者不爱,怀乡或是反思,都很难以一元化方式定义鲁迅的故乡情感。“鲁迅在个人生活上是抱着‘念旧’的价值观的,但他不愿让它上升到明确的意识层来。”何巧云称,可以尝试通过时间维度的梳理,发现鲁迅在明确意识之下埋藏着对故乡最真实的情感。综而言之,鲁迅对故乡的这种情感是复杂的,是变化的,在人生的不同际遇期对故乡的认识与感触皆不同。
对此,评议人荣挺进在小组总结时称,从故乡这个角度去解析鲁迅与当代作家的作品,恰恰是大时代背景下城乡二元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主题。鲁迅对待故乡的复杂情感,及张永辉三个故乡的提法也是今天的人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,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映时代主题永不过时。
五四女作家的“娜拉书写” 始终未冲破传统妇女家庭观念局囿
作为当下新时代的青年女性,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唐娒嘉以《众生喧哗背后:五四女作家的“娜拉书写”》为题,关注五四女作家集体建构的“娜拉书写”背后的文化心理与文坛生态,并对早期妇女解放进程中的困境与冲突进行了阐释和分析。
五四时期,易卜生的话剧《玩偶之家》传到中国后,女主角娜拉被塑造成新女性的代言人,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与旗帜,她的离家出走,构成和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方式。最先发声的是男性作家,鲁迅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及小说《伤逝》中塑造了“子君”这样一个娜拉形象,申说了对于“娜拉出路”问题的理解。胡适在《贞操问题》、《李超传》等文中也表达了自己的妇女问题观。社会媒介更是众声喧哗,好不热闹。周作人的《妇女运动与常识》、罗家伦的《妇女解放》、向警予的《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》、邓春兰的《妇女解放声中之障碍及补救方法》等数十篇文章,共同构成了妇女解放问题的大讨论。
冰心
与此同时,冰心、庐隐、陈衡哲、冯沅君、凌叔华、石评梅、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群体也开始言说自身困境与复杂心声。除陈衡哲年纪稍长外,这批女作家出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酝酿、到高潮再至落潮的前后十年,且基本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(庐隐、石评梅、冯沅君、苏雪林)和燕京大学(冰心、凌叔华)两所高校为群落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群,她们的登上文坛,宣告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不再湮没无声,她们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文学评论等一系列创作,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妇女解放过程中的风貌与困境。
“对娜拉的书写,对新女性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种种表现,对旧家庭中女性意识觉醒的太太奶奶们的情状展现,成为这些女作家们共同关注的重要素材。”唐娒嘉说道,娜拉式出走,成为反抗意识萌生的新女性跨出旧家庭的第一步,然而出走之后路在何方,也成为五四女作家的共同焦虑和现实难题。
凌叔华
在唐娒嘉看来,五四女作家的共同焦虑表现在她们笔下,似乎难有爱情、自由、学业兼得的情况。她们认识到女性在求爱与求学形成冲突时很难两全的现实处境,为了维系爱情、经营家庭,就只能放弃求学、抛弃学艺;为了学艺进取、有所奋斗,就只能割舍家庭、失去爱情。凌叔华的选择倾向于女子的个人奋斗,她的小家庭和爱情被搁置,她笔下的女主绮霞幻想着丈夫等自己学成归来,然而现实却冰冷无情,丈夫已另觅新欢。冰心对于新“贤妻良母”和“家庭”的温情呼唤,庐隐情智冲突下的停滞不前与犹疑善感,亦或是陈衡哲的勇于抗争与突破进取,众声喧哗的主张与选择,无不彰显着五四女作家们关于“娜拉”困境的现身说法。
唐娒嘉认为,在五四时代的中国,娜拉被塑造为新女性的代言人,鼓舞当时的新女性反抗传统,对妇女解放发挥了相当的启迪作用。然而五四女作家对创作的思考和人物出路的设定,始终没有冲破传统妇女家庭观念的局囿,唯一言明的出路,也只是以文字为武器,划归出一个适合新女性的安全地带——通过在文学领域的发展,施展才华和能力。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
编辑/崔巍